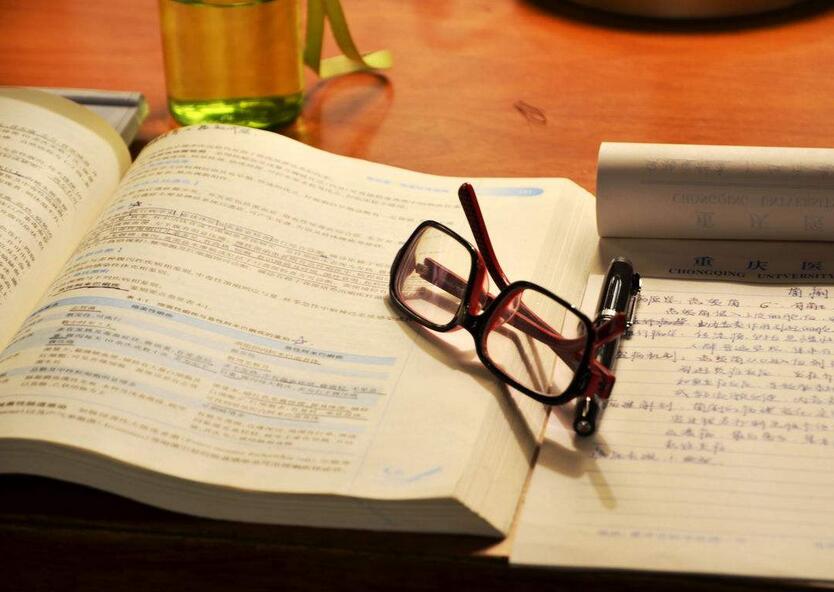辽金史料的深翻与检讨:转变“常识”,尝试“减法”

《辽史》
康鹏主要谈论了民族语言文字资料对于深化辽金史研究的重要价值。契丹、女真王朝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前人研究主要依据的是汉文的传世文献,无论是中原王朝的史书记载,还是辽金王朝编纂的国史,仅仅看汉文的历史书写往往是片面的,无法充分理解辽金王朝的某些特殊性,这就需要依靠契丹女真语言文字资料的解读与研究。例如,刘浦江老师研究的契丹父子连名制问题(《契丹名、字初释——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父子连名制》,《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此前研究者已意识到契丹人的第二名很特殊,但如果没有契丹文字资料,我们是无法知晓其规律性的。又如,从汉文记载来看,契丹人的姓氏只有耶律和萧两姓,但实际上,萧姓在契丹文字中是没有的,目前契丹大小字石刻记载的都是这些萧姓契丹人的具体部族名,如述律、拔里、乙室己等,由此看来,萧姓可能是对汉人的一种宣称,同时又是凝聚其他民族的一个工具,如奚人皆姓萧。再如,辽朝国号问题,汉文记载辽朝曾多次改国号为“辽”或“契丹”,但据契丹文墓志可知,辽朝始终实行双国号制,称“辽·契丹”或“契丹·辽”(刘凤翥《契丹文字中辽代双国号解读的历程》,《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2008年)。以上这些例证表明,通过将汉文记载与契丹文字资料相结合进行研究,我们可以深入了解契丹人独特的想法。此外,需要注意的是,现存的契丹语言文字资料除了契丹大小字墓志以外,在域外文献中也有可能保存一些零星记载,如《马卫集》等阿拉伯文献。总之,契丹语言文字资料还有很大的深入挖掘空间,而且它们恰恰可以从契丹人的角度去理解辽朝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值得大家关注和利用。
在三位受邀嘉宾发言之中,进入自由讨论环节。张帆教授对于孙昊、苗润博从史料“减法”的批判视角来检讨辽金早期的民族发展线索、建国道路等问题表示赞赏和支持。按说有关辽金早期历史的资料很少,十分珍贵,但经过他们的批判和剥离之后,也许反而能呈现出比原来更加清晰的画面,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不过,这种研究方法不一定对其他民族史研究也适用,比如蒙元的历史记载可能就不大容易进行剥离。由于辽朝流传下来的资料很少,《辽史》成书很晚,在编纂过程中会加入许多错误的历史知识,甚至是史官的比附、猜测与想象,所以《辽史》叙述的契丹早期历史很可能与契丹人真实的历史不是一回事。《金史》情况稍好,但也有一些后世史官建构的成分。而元朝有成书很早的《蒙古秘史》,尚未受到中原王朝观念的影响,其记载相对比较可靠,恐怕暂时还无法对其加以批判和剥离,这有待于今后的学术发展。同时,张帆教授还提示应关注金朝作为中原历代王朝中的一环,如何与此前的唐宋及之后的元朝相接轨与过渡的问题,并深入体会和解读史料背后的历史信息。历史总是比我们想象得要复杂,有些问题看似是不证自明的“常识”,但如果深入考究之后,或许会完全颠覆我们的既有印象。另外,对于初涉史学者而言,史料批判、剥离式的研究方法需小心谨慎,应在充分读懂、理解史料的基础上再追求创新。
包伟民教授并不觉得史料的多寡是一个问题,对于同一个学者群而言,面对同样的材料,如何做出出类拔萃的研究才是关键,这也是一种考验。有的断代史资料太多也有自身的问题,学者研究往往会流于资料的排比,而疏于深入解读,比如宋史研究对资料的解读总体上不如唐史研究精心。关于民族早期历史的叙述多虚无缥缈,有较多后人建构的内容,其实这种现象是具有普遍性的,在其他历史中也常常存在。以浙江龙泉民国司法档案所见为例,司法诉讼双方呈交的契约如何书写受到诉讼制度、法律条文、具体情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必须了解文本背后的书写目的。又如地方大族往往会有意地将捏造的本宗族、家族历史塞入地方志的编纂之中,等若干年后编修家谱时再从方志中抄出,这样私志摇身一变就成为官修“信史”。因此,在了解了某些通例和制度之后,再去谈史料的“减法”问题可能更为妥帖。包伟民教授还指出,以前我们往往会不假思索地接受前辈学者建构起来的说法,很少提出质疑,然而随着学术的发展以及研究条件、手段的进步,思考中国史学如何继续往前推进,除了开拓新领域之外,其实已到了对以往习以为常的成说进行检验和反思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