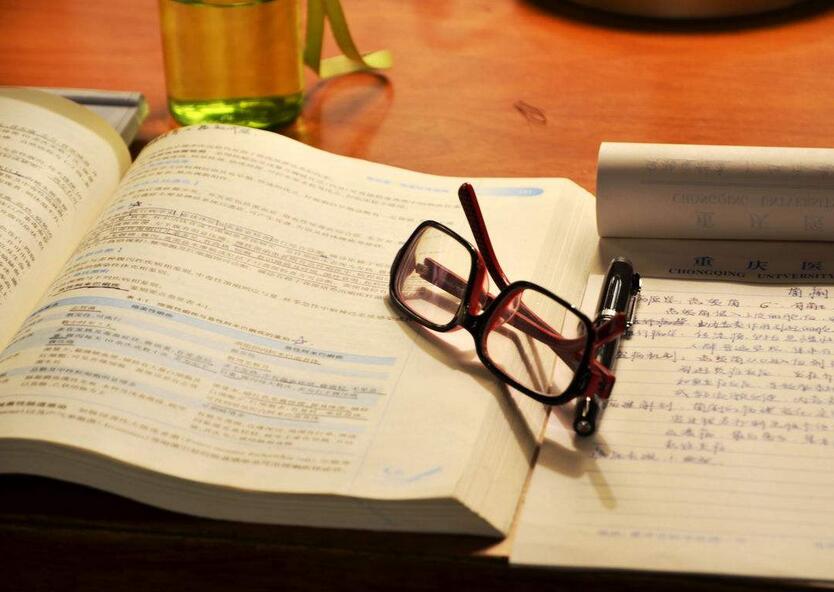辽金史料的深翻与检讨:转变“常识”,尝试“减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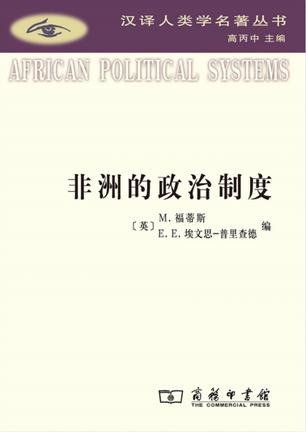
《非洲的政治制度》
苗润博将引言人所说的开拓新史料、对既有史料的深入考索和重新解读三方面问题概括为史料的“加法”与“减法”。在一般情况下的历史研究,或者说是积累阶段的历史研究,需要做的往往是史料的“加法”。就是多一条材料,我们的解释力似乎就多了一点;看到一个系统记载,就以其作为纲目,在此基础骨架上填充血肉,即搜罗更多材料证明已有的叙述和知识。这似乎是历史研究一个比较通行的做法。而所谓“深翻”在一定程度上是要做“减法”。我们一方面可能会面对支离破碎的史料,另一方面还可能要面对史料背后透露出的整体叙述。一种历史叙述的整体性、连续性越强,越容易被我们先入为主地接收,然而这样的历史叙述其实更加需要警惕。面对看似整饬的历史叙述,我们要做的首要工作应该是抽丝剥茧、正本清源,通过区分不同叙述主体、不同来源的史料,剔除干扰性因素,必要时需要以打破既有历史叙述连续性的方式来求得新的连续性。
以他研究的早期契丹史为例,“契丹”一名在公元4世纪末出现,直至公元10世纪初建立契丹王朝(即辽朝),建国前史大概有五百多年,以往我们讲述这段历史时,很多时候是以元修《辽史》关于这五百多年的历史叙述为依据,将其作为一种“常识”或者研究的基础。但如果深入分析这套历史叙述,不禁会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辽朝契丹人究竟是如何看待自己建国以前的历史?元朝史官所总结的发展脉络是否符合辽朝当时人的历史记忆或曰历史叙述?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意识落实到具体操作层面时,我们就要进行史源学的考索:元朝史官有关契丹早期历史的叙述是怎样形成的?实际上,这套历史叙述有两个不同的文献来源:首先是中原文献呈现了一套关于契丹早期历史的系统叙述,从《魏书》开始设置《契丹传》,到唐宋时期正史一直相沿不辍;其次是,元朝史官修《辽史》时尚能看到少量零星的辽朝人自身的历史叙述。出于一元线性历史叙述的思维习惯,元人理所当然地将辽朝文献和中原文献所记建国以前的契丹历史叙述进行了杂糅和拼接,在这一过程中会产生很多问题。苗润博的研究首先就要将我们熟悉的历史叙述进行拆分,做史料的“减法”,去除掉能够确定出自中原文献系统的记载以及元朝史官根据己见所做的削足适履、生搬硬套式的嫁接、粘合与改编。当把中原文献对契丹早期史的记载与元朝史官关于契丹早期史的想象剥除之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还原或保留辽朝自身的历史叙述。这时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辽朝自身的历史叙述居然与我们在《辽史》和中原文献中所见的完全是两种不同的面貌,这就是“减法”的作用。在层层剥离史料的过程中,传统史源学的追索与现代问题意识的结合显得尤为重要。
此外,苗润博还回应了民族史研究中的“汉化”命题。最近有学者试图用一种新的视角来重新解释辽朝整个历史的发展,提出自辽太祖阿保机开始便采用全盘汉化的建国方略。但根据苗润博的研究,我们在《辽史》中看到的辽朝中前期历史其实经过了辽后期的改写和重塑。汉化渐深的后期史官有意对辽朝开国历史进行了伪造和建构,并重新书写了辽中前期的历史叙述。如果不加批判地采信这样一套叙述去研究阿保机时代及辽朝中前期的历史,我们就会在不知不觉间充当了辽朝后期史官的现代翻译者,而不是批判者。
苗润博总结道,在中国古代断代史研究的许多领域纷纷超越传统精耕细作阶段,进入后现代的史学反思即思考历史书写这一层面的问题时,辽金史研究某种程度上还在前现代和后现代之间徘徊,在史料“加法”还未做好的情况下,同时要面临做“减法”的问题。不过,反过来说,辽金史研究也有后发优势,可以有意识地借鉴后现代或是比较成熟的其他断代史的研究方式,立中有破,破中有立。在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或许不是史料的“加法”而是“减法”,毕竟对于辽金史学者而言,史料的“加法”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而史料的“减法”则是义不容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