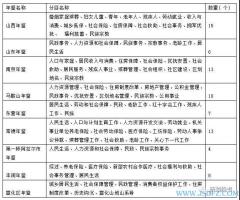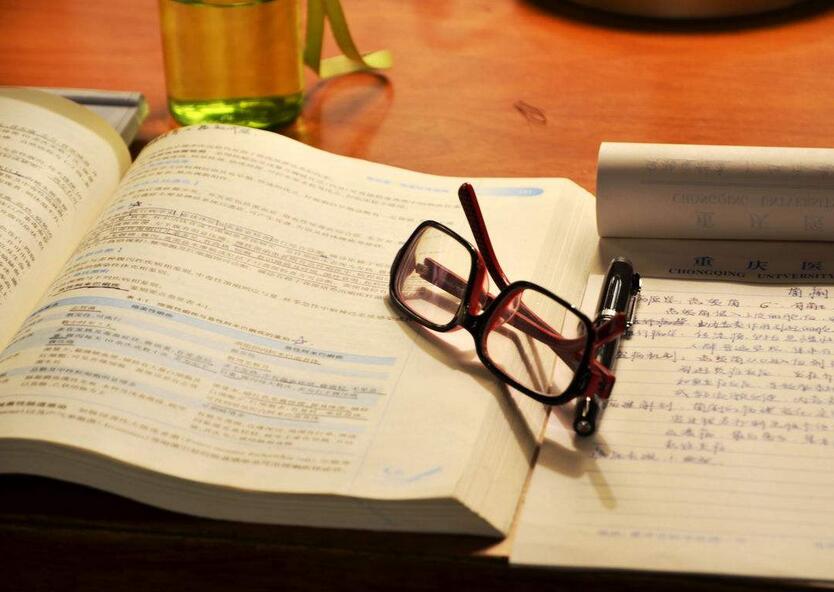利用乱·错·简·散的正史地理志,需要注意什么

沈约以后的后世史家,但凡涉足魏晋南北朝政区者,也是顺着休文的语境,或顺流而下,或顺杆而上。如自我感觉极佳的清儒王鸣盛,既以“人欲考古,必先明地理,地理既明,于古形势情事皆如目睹……此其所以为通儒也”自勉,并且炫耀“予撰 《十七史商榷》百卷,一切典故,无所不考,而其所尤尽心者,地理也”,又说“汉末天下三分,陈寿不作表志,兹事已难研究。晋一统裁二十三年,当惠帝太安二年而僭伪并起……直至隋文帝开皇九年始合为一。自太安二年至此,凡二百八十七年,区宇分裂未有甚于此时者也,故地理为最难明”(《东晋南北朝舆地表·序》),于是在《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七中专立“南北地理得其大概不必细求”条,明确指出两晋南北朝政区“纠缠舛错,不可爬梳,其势然也…… (沈)约身居齐、梁犹如此,况去之又千余年乎”,却仍以卷五十七整卷的篇幅,“细求”南朝地理,虽然没有求出什么,或者求出的都是人所共知者,至于人所不知者,求出的又往往是错的。
其实如王鸣盛这样的言行“矛盾”———言则强调很难,行则知难而进,藉以彰显才识,在乾嘉诸儒的著述中可谓屡见不鲜。如洪亮吉既归纳了补三国地理的“十难”,又努力完成了《补三国疆域志》;既“笑纳”了钱大昕感叹的补东晋地理的“四难”,又“凡两阅岁而成”《东晋疆域志》。有趣的是,这样的虽难亦行,竟至成了相关著述之序言、绪论的常规路数。远如洪亮吉之子洪齮孙的 《补梁疆域志》,李兆洛为之序云:“先生自序补三国疆域志,谓有十难……然以梁校之,为尤难也”;近如王仲荦 《北周地理志》 (中华书局1980年版),“序言”中罗列了十点“补北周地理志遇到的困难”,这还不包括“在写定本书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还多,这里就不多谈了”;再近如施和金的《北齐地理志》(中华书局2008年版),其“绪言”指出:王仲荦所说的“十大困难,都是切身的体会,也是经验之谈。这十大困难,编写《北齐地理志》时同样要一一遇到”。
那么,从乾嘉考据到近今朴学都在反复强调的“难”,究竟难在哪里呢? 质言之,并不难在魏晋南北朝政区本身的复杂,因为在诸多朴学考据大家那里,较之更为复杂的问题,都取得了堪称丰硕甚至优秀的研究实绩;而反观魏晋南北朝政区的研究,真正能够取信于人的成果,实在不多,即以收入《二十五史补编》的诸家补志补表言,笔者浸淫其中多年而得的感觉是,有关三国的三家,符合后来者居上的一般情形,即吴增仅的《三国郡县表》胜过谢钟英的《三国疆域表》,谢钟英的《三国疆域表》又胜过洪亮吉的《补三国疆域志》;有关东晋南朝的诸从事先秦史研究,既要求研究者具备古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考古学等方面的素质,又要求研究者具备竭泽而渔的史料搜集功夫,并养成不盲从后世注疏家解释的习惯;
从事明清研究,则要练出从恒河之沙一般的文献资料中披沙拣金乃至点石成金的本领,还要有足够的体力,能到藏书机构、到田野广泛采集关键或独特的文献。
而具体到三国两晋南朝政区的研究,从事者首先需要掂量掂量自己的素质、性情是否适合于处理这“乱”、“错”、“简”、“散”的文献资料。
家,则质量由好到差可以做出这样的排列:臧励龢(民国)《补陈疆域志》、洪齮孙《补梁疆域志》、洪亮吉《东晋疆域志》、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然而即便是排序最前的吴增仅《三国郡县表》、臧励龢 (民国)《补陈疆域志》,孔祥军曾例举吴《表》存在“郡县归属失考、郡县名称失考、误引文献、诸州郡县置废失考、侯国建置失考”五个方面的谬误 (《汉唐地理志考校》,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版),谭其骧师曾作 《 校补》(《禹贡半月刊》第五卷第六期,1936年),“凡得可资校补者百余条”,又归纳出“臧书体制有未尽善者……七端”,金麟 (施和金)再作《订补》(《历史地理》第19辑,2003年)47条。如此,排序最后的洪亮吉 《补三国疆域志》、徐文范 《东晋南北朝舆地表》之质量,又可想而知了。
在这里,笔者并不是要呵责古人,前贤们勤搜博采、钩沉稽遗、排比考证,所汇集的资料以及部分研究成果,当然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而之所以古人前贤的补志补表仍然不能令人满意,根本的原因在于文献资料的制约。其实,无论是洪亮吉的“十难”、钱大昕的“四难”,还是李兆洛的“尤难”、王仲荦的十点困难,说来说去,关键的难点、倍感无奈的困难,还是文献资料的困难。笔者在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三国两晋南朝卷》“绪言”的最后,同样检讨“尽管我们广事搜集、尽力考证传世文献资料,并辅以文物考古资料的补充与印证,但还是有不少的时代 (比如梁朝、陈朝)与诸多的地区 (尤其边疆地区、疆域频繁易手地区),政区的面貌及其变迁情况难以全面地或者准确地复原”,原因同样无他,可资利用的文献资料的缺失、矛盾与散乱也。
三 国两晋南朝政区研究中文献资料的缺失、矛盾与散乱,不妨先以内容最为丰富、总体评价也相对最高的《宋书·州郡志》(以下简称《宋志》)为例,予以说明。
《宋志》四卷,是沈约“以班固、马彪二志,太康、元康定户,王隐《地道》,晋世《起居》,《永初郡国》,何、徐 《州郡》 及地理杂书,互相考覆”而成的,沈约所做的主要工作,是“凡诸记注,悉加推讨,随条辨析,使悉该详”。就其工作底本看,多取何承天、徐爰两家 《宋书·州郡志》。何承天 《志》 迄于元嘉二十年 (443),徐爰《志》止于大明 (457—464) 之末,沈约《宋志》也是“大较以孝武大明八年为正,其后分派,随事记列。内史、侯、相,则以昇明末为定焉”,如此可以推知,沈约《宋志》盖因徐《志》 之旧,而补载宋末之事,又多记何《志》、徐《志》异同。而由于“考覆”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司马彪的《续汉书·郡国志》,《宋志》所述沿革颇多追至两汉;其“考覆”的晋、宋地志如 《晋太康三年地志》、东晋王隐《晋书·地道志》、宋 《永初郡国志》 等,则分别为西晋、东晋与刘宋初年纪录;又“三国无志,事出帝纪,虽立郡时见,而置县不书”,沈约“以《续汉郡国》校《太康地志》,参伍异同,用相征验”。至于《宋志》中所引的“地理杂书”,则有《吴地志》《会稽记》《吴录》《广州记》等等。如此的众多史籍之“互相考覆”,保证了沈约《宋志》所述政区建置与沿革既较为系统、全面,州郡户口、水陆道里的记载也较为详备。
然而另一方面,据上所述成志过程,则从某种意义上说,《宋志》又是沈约依据各类资料编撰的一篇论文。沈约虽有文才、史识、为政经历,专门的地理沿革之学却非其所长,当时政区又非常混乱,所以《宋志》的编撰难度确实很大。而就笔者的研读体会,《宋志》存在着三个影响全局的最突出问题:
其一,断限不严。《宋志》最重要的志例之一,是州郡县的记载“大较以大明八年为正”,其实断限并不严格。如所载的二十二州,有泰始六年 (470) 所置的司州、越州,却无大明八年 (464) 时存在的东扬州。又各州所领郡县,也多非大明八年制度。如徐州“今领郡三”,“今”指元徽元年 (473);南豫州刺史“今领郡十九”,谓泰始 (465—471)末年南豫州、豫州计领十九郡;荆州刺史“今领郡十二”,“今”为泰始三年;湘州刺史“领郡十,县六十二”,数之则六十六县,多出的四县,为元徽二年所立的湘阴,“宋末立”的抚宁、乐化左县,“宋末度”的建陵,所以湘州的郡县领属实以宋末为断;雍州刺史“今领郡十七,县六十”,数之为郡十七,县六十八,其中晚于大明八年者,有泰始末所立的北河南郡 (领县八),宋明帝末立的弘农郡 (领县三),故雍州实以宋明帝泰始末年为断限。交州的标准年代也不是大明八年,如所领义昌郡“宋末立”,而大明八年时属交州的合浦郡、宋寿郡,志中却属泰始七年始立的越州。据此,可以说《宋志》事实上并无某一特定的标准年代。
其二,为例不纯。如《宋志》在州郡下多记水陆道里,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二十三云:“休文志州郡,于诸州书去京都水陆若干,于诸郡则书去州水陆若干、去京都水陆若干,唯州所治郡,不云去京都水陆若干者,已见于州也。南徐州领郡十七,南东海为州所治,此外则南琅邪、晋陵、义兴皆有实土,故有水陆里数,南兰陵以下十三郡,有户口而无水陆里数者,侨寓无实土也。诸州皆仿此。”按钱氏此条颇具卓识,它为我们根据《宋志》所载水陆道里,判断州郡是否侨置、侨置是否改为实土,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但是细检志文,实土州郡有失书水陆道里者,又有侨郡已割为实土、而水陆道里仍缺书者。由此造成的麻烦是,依据《宋志》有无水陆道里判断州郡县有无实土,又不可一概而论。
其三,彼此矛盾。最明显者如户口数字与郡县数目。《宋志》各州小序中所说的户口数,与该州各郡户口数之和,只有郢州是相合的,其他都不一样;《宋志》 各州小序中所说的郡县数,以及各郡所说的县数,也与各州实列郡县数、各郡实列县数常有出入。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呢?其原因在于年代断限不严格及所据材料来源不一致两个方面。如据何德章的札记,《宋志》各州所列户口总数反映的是大明八年的状况,而各郡户口数则是宋末的数字,具体是“宋末”的哪一年,又难以确定。这方面的情况再往下说,就更加复杂了。如《宋志》所载户口数,既有土著户口,也有侨流户口,侨流户口又包括经过土断的黄籍户口与未经土断的白籍户口,就其准确性来说,土著黄籍户口数胜过侨流黄籍户口数,侨流黄籍户口数又胜过侨流白籍户口数,如此,我们要做刘宋户口的文章,对于《宋志》这份珍贵的人口资料,就得进行分别处理,而分别处理的难度又极大。
当然,除了以上这三大问题外,《宋志》中属于沈约原本的各样问题还有许多,如记载疏漏、考辨讹误、叙次不清;若再加上传抄过程中出现的夺误讹衍,今天 《宋书》 通行本亦即中华书局点校本存在的各样错误,则引证 《宋志》之前我们必须先做的考证工作,就势必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而针对四卷《宋志》中的以上各类问题,笔者在拙著《六朝疆域与政区研究》(增订本,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中,专门安排了“《宋书·州郡志》 献疑”作为附录,整理出178条札记;在《宋书州郡志汇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的“代序”中,笔者更是说出了这样的狠话:“《宋书·州郡志》本身的失误、流传过程中产生的失误、中华本校点中存在的失误,共同决定了 《宋书·州郡志》 成为不能拿来就用的重要文献”,“如果不甚明了这些问题,不但《宋书·州郡志》 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难以充分发挥出来,而且严重者还会误读误用史料,或者根本就无法理解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