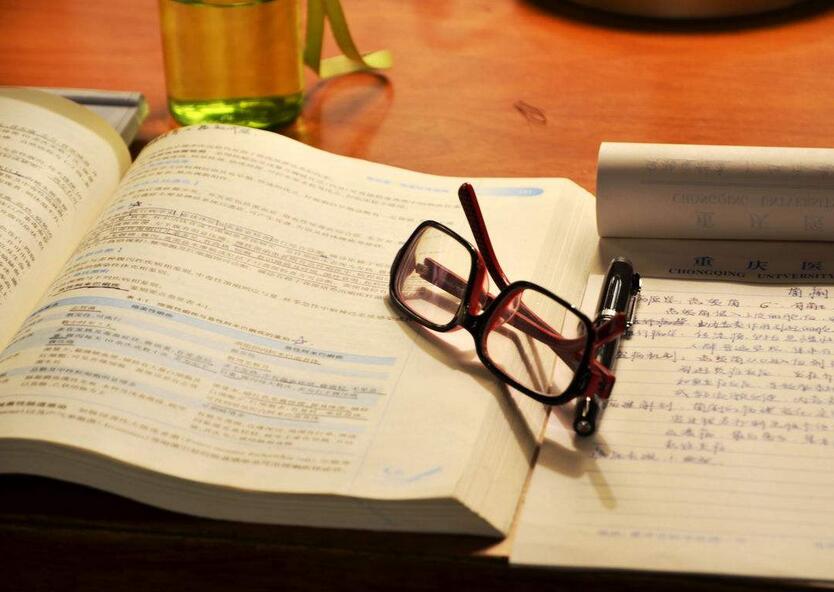康熙《杏花村志》对名村志编纂的借鉴
晚唐杜牧所作《清明》一出,杏花村闻名于世。由于具有极高的文化内涵和品牌价值,杏花村的确切地点一直众说纷纭。清康熙年间,郎遂编纂池州《杏花村志》十二卷,被收入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文献《四库全书》。以志为证,池州杏花村止诉息争,赢得正宗之名。郎遂(1654—约1739)字赵客,号西樵子,一号杏花村,贵池(今池州)杏花村人,清代文学家、诗人。少年由诸生入太学,以诗文名于时。郎遂不乐仕途,出于对乡土的热爱,自康熙十三年(1674年)开始编纂《杏花村志》,历时11年,至康熙二十四年夏授梓成书。编纂村志作为我国最基层文化的真实记述,对抢救传统文化、保存文化遗产、留存珍贵资料、建设美好乡村,意义重大。无论是在篇目内容、资料收集、体例规范,还是史料考证、文字记述、体现特色上,康熙《杏花村志》对名村志编纂都有很强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一、为何要编名村志
地方志编纂源远流长,村志也是地方志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员。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伴随着城市化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乡村历史文化的传承延续,面临着几千年来所没有的巨大挑战。守护乡村文化的命脉,守住华夏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成为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呼声。村志编纂,以志书的形式记载历史,留存记忆,已渐成为回应呼声的最好关切。
(一)国家文化战略的需要
党中央、国务院一直十分关心重视地方志工作。2015年8月国务院印发《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在主要任务中指出“重视军事、武警及其他各类专业志鉴、民族地区地方志、乡镇村志和地方史编纂工作。”“指导有条件的乡镇(街道)、村(社区)做好志书编纂工作,做好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组织编纂工作。”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是《规划纲要》部署的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是国家明确要求必须完成的一项重大任务。通过村志编修记录乡村状况及变迁,追溯乡土事物的由来,可以将已经消失或即将消失的村落的历史记载下来,将村落各方面的信息留存下来。名村志编纂是挽救乡村文明、保留乡土记忆、留住文化遗产,为村民建筑精神家园的有效方式。
(二)地方志自身的需要
在我国志苑中,自古就有县志、州志、府志、通志、山水志。而为一村修志,时间并非长久,成果也就最近才显丰硕。郎遂《杏花村志》问世后,世人盛誉为“开编纂村志之先河”。“清代村志 9 种、民国村志 14 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修村志 600 多种。”[1]《杏花村志》问世后,至乾隆年间,经浙江巡抚三宝采集,呈进清廷“四库馆”。经总纂官纪昀审核,作为全国唯一村级志书被收入《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七史部三十三地理存目六《贵池先哲遗书》第二十五种。价值之高,桃李不言。全国第二轮修志以来,各级志书接踵出版,其中“乡镇、村志编修方兴未艾,累计出版4000余部”。[2]广州市天河区全区25个村,甚至村村编村志。编纂名村志,薪火相传,丰富了志苑种类,是地方志自身发展的需要。
(三)地域文化传承的需要
地域文化需要通过志书来传承,更需要通过志书来确认。杏花村因杜牧《清明》诗作而声誉鹊起,享誉海内外。虽然“明、清以来大量权威史料的肯定性记述,如《池州府志》《贵池县志》《杏花村志》及清代官方的《江南通志》,等等”。[3]但是,由于杏花村太过于出名了,仍有不同声音来搅和,所以迫切需要志书来定性,需要志书来传承。“从1985年到2001年,在这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村落的个数由于城镇化和村庄兼并等原因,从940617个锐减到709257个。仅2001年一年,中国那些延续了数千年的村落,就比2000年减少了25458个,平均每天减少约70个。”[4]面对日益消逝的村庄,编纂名村志就是要将这些历史文化传承下来,让人们记住乡愁,不忘乡情。朗遂对杏花村的“山水之秀、花卉之盛、村落之古、人文之萃”,如数家珍;对杜牧吟诗《清明》、问酒杏花村,骄傲不已。郎遂生于斯、长于斯、歌哭于斯,对家乡充满深情,常虑杏花村如无文字记载则会“久而莫识所传”。由此广征博采而成《杏花村志》,既一排众议,又得以延续山水名胜。
(四)村民内心的需要
郎遂世代居住在杏花村,家乡的秀山丽水、名人胜迹、文物建置,都凝聚着郎遂先辈的辛勤付出。“郎遂先祖文韶公,博洽多文,官至宋奉议大夫,入元时归隐杏花村,卜筑焕园于玉台山麓,建聚星楼藏书充栋,其子孙繁衍聚族而居。至今其地曰郎家冲”。[5]郎遂为文韶公第十三代孙。一生耄而好学,著述等身,留下《池阳韵记》《焕园诗略》《池州诗史》《池州历朝文选》《杉山志》和《杏花村志》等15种著述。郎遂以为“齐山当城之南……旧有志”,而九华山亦有志。城西杏花村成于古,名于时,“而杏花村志缺也,遂村人也,乃纪所闻以志之”。又为防先祖功德“恐湮没而不张”,遂发自内心的强烈愿望而决定编纂村志。 “在建设美丽乡村中,河北省邢台市把留住村庄的历史文脉作为一项重要内容,通过编纂志书、建村史馆等举措,将独特的村庄文化永久记录下来,激励后人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6]相反,如果没有名村志文化载体的传承,“纵使村民的腰包装得再鼓,宅院建得再高档,祖坟修得再豪华,但在乡土历史文化的原野上,他们仍是手足无措的“失地者”;在精神和灵魂的寄托上,仍有无处依凭的感觉。”[7]